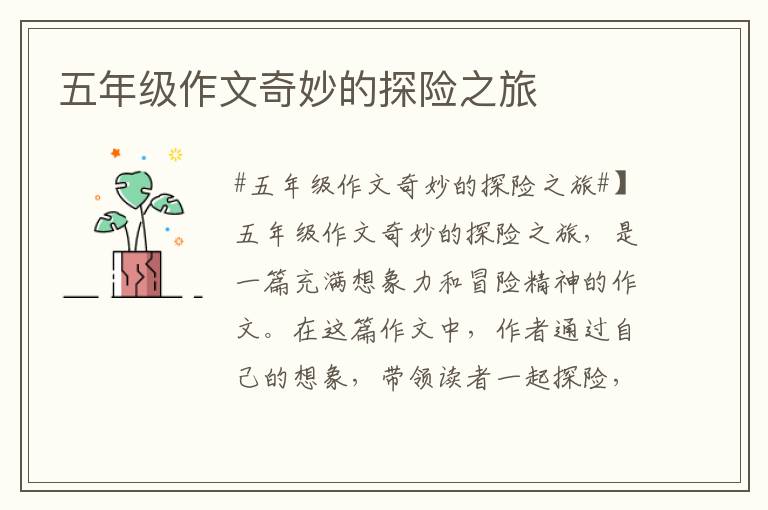風雪八千里作文1300字

時序已三月,而風雪仍是紛紛。紛紛在愛荷華極目不盡的大平原。 我們一家四口,決定于三月一日離開愛荷華前往舊金山的對岸—柏克萊。我已經結束了此地的研究,按情形我知道必得走,但令人猶豫的是走法。
一是坐飛機,一是自己開車。我心巾早有決定,就是開車,而邀我工作的主人以及友好們卻逼我改變計劃。 我知道離這兒到柏克萊的路很遠,照我們東方的里程算起來,約合八千里。但這條八干里路,并非普普通通的云和月,而是很多高山峻嶺與漠漠砂地,路上非經過落磯山脈與內華達沙漠不可。
再加上雪季還沒有滅衰,如果路上遇到雪崩,難免有危機了。很可能不是跟著雪崩一起滾落,就是引擎發不動,只好凍死了。 這幾天,我反而勸誘他(她)們準許我開車西行。我以“八十號公路的重要性”辯解,再以小心開車的態度來征求他(她)們的原諒。
最后取得了保羅·安格爾的支持,一向體貼的安夫人與我的同胞朱教授也只好追認,但她們也是一副忐忑不安的樣子,無可奈何狀。 既已決定,心里難免暗自害怕,真的任重道遠了。一家四口的生死,全在于我,八千里路的風雪,難以預測。能夠下這么一個決心,并非靠長期的考驗與踏實的技術,靠的是吊兒郎當的浪癖,可以說百分之九十是浪癖所帶來的決定。
三月一日清早,朱教授請我一家四口到她家里吃早點,并為我們餞行。她另請詩人安格爾夫妻。那天,積雪上又下了新雪,但八十號公路上的車子穿梭不停。我們七個人,吃得盡興,主人的烹飪,贏得了口碑。
大家說個不停,七人之間,雖然摻雜了英、中、朝語等三種語言,但融洽無間。 我們三家人,常在一起,共吃一個火鍋,翻跳一個陽臺。
我們在一起瞄準過西沉的太陽,滾落過積厚的雪堆,打發過漫長的冬天,也烤過火紅的壁爐。尤其安夫人—華等,待我如弟,照顧我無微不至。 吃飽了飯,我一股勁兒站起來,便說;“我們該走喲!” 我勉強抑住悵然的別懷。華菩姊與朱教授的眼簾里已經潮濕濕的。
妻子與兩個女兒,也跟著站起來,緊張地望著我。我走出幾步,她們急著穿靴。我先去開車門,而且猛然發動引擎,引擎已經轟隆隆地響著。我和家人一個一個上車,安格爾夫妻站在車旁,朱教授遞給我一大包東西。
“這里裝的是各種小吃,路上慢慢吃。”她邊遞邊說。 “這是一盒蠟燭。請不要以小見笑。
路上,如果遇難,請點燭取暖!一根蠟燭在雪崩中救人的奇跡,不是沒有的喲!” 我敬領,踩了油門,車子跳動了一下。我很想趕緊躲閃這么傷感的焦點,免得有揮淚的場面。朝外揮揮手彎彎腰,我一家四口的車子,已開出了這個我們帶來做食客的院子。回首一看他們三位橫排,修長的保羅,站在中間,伸直了兩個臂膊,用右手的兩個指頭,做出V字的手勢,而她們兩位勇徽授,忙著擦眼淚。
等走上了八十號公路,我才放聲大哭,一直開到愛荷華州的邊界熱淚未涸過。我們當初落地,各在異地,而且隔得好遠,而今天萍水相逢,風雪霏霏,惠好相從,所謂親如弟兄何必骨肉親呢? 頭一夜,我們住在內布拉斯加的首府,第二天走過了內布拉斯加的茫茫平原,第三天穿越了懷俄明與猶塔的高原與千重山巒,第四天開了萬山鳥飛絕的內華達沙漠,第五天下午才駛進了桃李爭艷的春光—北加州柏克萊。 這五天,一共開了八千里路,路上雖然常被風雪擋路,視線茫茫,但從未迷路,更沒有翻車,究竟是安全抵達。頂多,我是一個橇板給梅鹿拉著的感覺而已。
這五天來,每逢大雪,就想起一盒蠟燭;每感孤寂,就想起愛荷華的“三人組”。想起他們,渾身都暖熱起來。